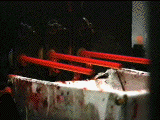.jpg)

热点排行
“千人糕”与“小铅笔”
面对小铅笔和千人糕的相同“家谱”,中西方学者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50年代出生的人们或许会记得,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我们这茬人都学过一篇名叫《千人糕》的课文。虽已时过好几十年,但我仍想得起这篇课文的大意:
一天,叔叔带“我”到食堂吃“千人糕”,我想这种由上千人做的糕一定会很大很大,大到想不出来的程度,所以一路都在好奇地想这糕究竟有多大。不想到了食堂一看,才发现原来就是普普通通的蒸糕,一点儿都不大。这么小的糕怎么能叫“千人糕”呢?正当我迷惑不解的时候,一位炊事员叔叔过来对我解释说:别看这小小一块糕,它经过农民伯伯播种、管理、收割、脱粒,然后运到工厂去加工磨面。这磨面用的机器和电,又是由许许多多工人叔叔生产的,要采矿、炼钢炼铁,制造机器,要发电。磨成面粉以后,又用汽车运到粮店,最后才到食堂做成蒸糕,要蒸熟还要烧工人叔叔采的煤……这每一个环节、每一道工序又都涉及到其他许许多多的环节和工序,这些都要有好多好多人的参加才能完成,如果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这糕就做不成吃不成了,所以就叫“千人糕”。听了这番话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样一块小小的蒸糕真是要经过成千上万人的劳动才能做出来的!难怪要叫“千人糕”,叫“万人糕”都应该。
讲完课文后老师反复强调,这一课的目的实际是要告诉我们两个道理:一是一定要珍惜粮食,千万不要浪费大家的劳动成果;二是要记住所有的成果实际都是集体劳动的结果,个人的作用非常有限,个人千万不能自高自大,个人应该是集体大墙中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是集体机器中的一个零件、一个“螺丝钉”,一定要服从集体的安排,如果只想到个人利益,集体的大墙就会倒塌、集体的机器就无法正常运转……
几十年后,在读弗里德曼夫妇合著的《自由选择》一书时,意外地发现他们在书中引用的一个名为“小铅笔的家谱”这个小故事,内容与“千人糕”竟如出一辙。不过他们要说的“道理”,却与之非常不同。
“小铅笔的家谱”原文发表在1958年12月的美国《自由人》杂志,这篇文章以拟人的手法,用一个“普通木杆铅笔”的口气讲述了自己的来历,也就是自己的“家谱”。首先,做这支铅笔的木头是一棵长在北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的笔直的雪松,把它砍倒,运到站台需要“锯、卡车、绳子……和无数其他工具”。这些工具的制造过程又涉及到许多人和各种不同的专业分工技能:“先采矿、炼钢,然后才能制造出锯子、斧子和发动机;先得有人种麻,然后经过各道工序的加工,才制造出了又粗又结实的绳索;伐木场里要有床铺和食堂,……伐木工人喝的每一杯咖啡里面,就不知包含有多少人的劳动!”而后,木材被运到工厂锯成板条,再运到铅笔厂做成笔杆。笔芯是由从锡兰开出的石墨经过复杂的加工而成,其中又经过了不知多少人的努力。铅笔上的橡皮也是由产于东南亚一带的菜子油和硫氯化物反应而成的。经过许许多多数不清道不白的工序和环节后,这支“小铅笔”骄傲地说:“地球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怎样制造我”。
讲完这个故事后,弗里德曼夫妇便由此展开了自己的“道理”:直接间接参加制造铅笔的人成千上万,但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参加了这支铅笔的制造过程,而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取得自己所需要的货物和劳务的方法。这样,“每次我们到商店里去买一支铅笔,就是在用我们的一点点劳务去交换那制造铅笔的成千上万人的一小点劳务。”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没有谁坐在中央办公大楼里号令那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宪兵队来强制人们执行不曾发布过的命令,但竟然制造出了铅笔。这些人居住在许多地方,讲不同的语言,信不同的教,还可能互相仇视——但是这些区别全都不妨碍他们合作生产铅笔。这是怎么回事?”
这种“奇迹”的答案就是:如果双方的交换是自愿的,那就只有在他们都相信可以从中得益时,才会做成交易。也就是说,这种交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而不是一个得利另一个就必然受损。但如此众多的原本不相干的人却能如此协调一致地促进自己的利益,就在于有价格制度这个机制在起作用,协调千百万人的活动。有了这个机制就“无须中央指导、无须人们互相对话或互相喜好,就能完成这个任务。”也就是说,价格机制使“人们各自谋求自身利益,却能使每一个人都得益。”使许多“只盘算他自己的得益”的个人仿佛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达到一个与他的“盘算”并不相干的目的。
这两个故事非常相同,但双方看问题的角度、乃至思维方式却大相径庭,进而讲出来的道理自然非常不同,着实耐人寻味。倘对产生这种不同的原因作一番认真的思考和研究,当会给我们某种深刻而有意义的启示。当然,如果仅抽象地“论理”,或会感到双方确实各有各的“理”,彼此都不错。然而,正是这种“道不同”却导致了现实世界中社会、经济体制不仅“不相为谋”甚至截然相反。这种不同的体制,对社会、经济乃至每个人生活的不同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
(京报网__北京日报 ■雷 颐)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2007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