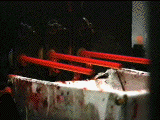.jpg)

热点排行
我们家的笔
在我们家,除了书多报多刊物多外,还有一样东西也是随处可见,那就是——笔。式样繁多,类型不同,色彩丰富——钢笔毛笔铅笔蘸水笔圆珠笔,红水笔蓝水笔黑水笔绿水笔,散放在书桌上,茶几上,夹在书刊中,插在笔筒里,可随时取用。
父亲辛笛喜欢给我们买笔,从学写字用的铅笔到圆珠笔到钢笔,几乎都是父亲给我们买的。记得最清楚的是在上世纪60年代,父亲在解放后很少发表诗作,有一次用他难得拿到的稿费给我们一人买了一支自来水笔,是当时最流行的新式样,包头铱金笔,吸墨水的部位与老式钢笔截然不同。我们拿到这么好看新奇的笔,雀跃起来。小姐姐圣珊和我忙着找墨水瓶打墨水,试试我们的新钢笔,而哥哥圣群坐在客厅的大餐桌旁一眨眼的工夫就把给他的笔拆得七零八落,动作之快让我们咋舌,惹得父亲大光其火:“跟你说过八百遍了,要爱惜东西,要爱惜东西,就是不入神,当作耳边风!”训斥儿子的语言也用文学夸张——“八百遍”,就像李白的“白发三千丈”一样。
父亲对笔的爱好以使用为目的。他写作写信时爱用笔尖细些的钢笔,适合他蝇头小楷的字体,看书报他认为重要的词语或段落上则爱用粗红铅笔勾画出来,读古典诗词在他欣赏的诗句下最喜欢用绿水笔画上小圈——绿色是他的最爱。他原先也喜用名牌笔,一支派克笔从解放前一直用到解放后,陪伴他写出不少诗文。但“文革”中把他大量的藏书连同心爱的派克笔一起抄走,他体验到李清照在金石图籍散失后的心境,悲愤无奈之余还能达观排解。在苦闷的岁月里他悄悄写旧体诗,与远在北京的钱钟书先生私下里唱和不断。那时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抄写他们的唱和之作。家里还留存有他用毛笔抄在老式水印信笺上的诗作,另有两本用钢笔抄写的练习簿,上面的笔迹已似淡墨山水,但透过流畅的笔画还是可以看出他抄写时兴致盎然。
晚年的父亲仍爱好各类笔。只是轮到儿女及孙辈给他买笔,或朋友从海外给他带来新笔。八九十年代流行不用吸墨水的水笔,父亲同样用得高兴,只是用完后还舍不得丢掉,结果家里到处都有急用时却写不出字的笔。
父亲在给人题字时往往坚持用毛笔,而母亲则是他书法的最好鉴赏人。母亲认为他的文人字自有特点,写核桃大的字最合适,所以他多用不全部化开的大楷笔。在那些阳光明媚日子里,上午客厅的光线比较好,母亲坐在大餐桌的一端,为父亲磨墨,看着他握笔一行行写来,那是家里很温馨的时刻。父亲写好后总拿起宣纸给母亲过目,请她作出评价,父亲很看重她的意见。直到母亲患骨质疏松症,已无法行走,精神不济时,只要把父亲写的字拿给她看,她还是能一眼就分辨出写得认真还是潦草:对写得好的,她会点头表示赞许;对写得差的,她会轻轻地说几个字:“又不舒服了!”确实,那正是父亲深感身体不适但为完成“题字任务”而仓促写就的。在母亲病重及去世后父亲连握毛笔的力气似乎都随母亲而去,他只用南京小友送他的毛笔式水笔题写,而且自认为写得再也不如毛笔字好了。
家里至今还留有一支绿杆金笔——浪琴牌,是父亲送给母亲的礼物。母亲一直用它备课、写信、翻译,后来笔杆已裂缝,母亲就用胶布裹起来继续使用。现在两位老人都已驾鹤西去,但爱情的象征——笔却还在,记忆着父亲诗作《蝴蝶、蜜蜂和常青树》中的相恋、成家、立业的故事。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王圣思
2007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