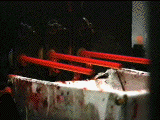.jpg)

热点排行
古董钢笔的故事
那天他来电话说,一位英国老朋友最近路过香港跟他朝夕话旧,日子过得又伤感又温暖。“是60年代我在苏格兰结识的美人。”他说,“她父亲那时候在Glasgow经营祖传的一家小铺子,专卖新旧名贵钢笔,兼卖一些讲制笔历史、讲penmanship的古董书籍。”早年我在剑桥旧书铺里也买过一些讲书法的旧书,认真读了也认真练了,英文字终归写不好,那是小时候描红copybook描得不用心,这辈子只能靠sloppy的独家行草吓唬人了。
“美人给我带来一管古董钢笔。”他说,“款式和做工都棒极了,简直是艺术品不是书写工具。星期天下午你来看看。”我去了,也看了,好漂亮的一件老古董,黑色笔管镶白金的花草图案十足WilliamMorris的缠枝画风,线条典丽灵动,布局丰盈而不妖冶。七十开外的老大哥惬意得像个初恋的小伙子,匆匆亮出两张梦里情人的老照片,忍不住又让我欣赏礼物盒里飘香的几行字。美人确实古典、精致;字也端庄,是美国老派仕女写惯的copybook字体,英国人的字练成这样的不多。
中国毛笔是公元前一千年的发明,大哥说公元前三百年古埃及人才学会用芦苇杆写字,公元7世纪塞维利亚古籍里有了鹅毛笔的记载。我想起伦敦书商朋友JamesWilson给我看过一枝鸟类羽毛做的古董笔,说是比鹅毛笔还要老。他沾了墨水让我试试,岁数太大,笔尖硬得写不出棱角了。威尔逊说金属做的笔和笔尖古希腊古罗马也有,大英博物馆仓库里一定找得到。他说他还有一管上世纪20年代的圆珠笔,写不出字了,当作历史那样供奉在玻璃柜子里。
威尔逊是笔痴,家藏无数历代名笔,我还送过他一管香港集大庄“天下为公”小楷毛笔,后来读了溥儒写给贾讷夫的信,我才知道这种毛笔也大有讲究。溥先生请贾先生替他买一批“天下为公”,说是新制旧制相差甚远,旧制管上刻着文清氏、杨振华等字,新制的只刻上“集大庄精制”,绝不能用。还说“天下为公”四字新旧也不同,“旧制者字小而规矩,新者散漫而字大,至不成形象。请据此数端选购其旧制者。”
我这位大哥老早懂得这些诀窍,他的毛笔小字写得潇洒,简直缩小了的王梦楼,留英归来跟沈从文通过信,客厅里至今还挂着沈先生一幅长长的条幅。沈从文这种条幅正是张充和先生来信里说的“极长极窄”、“没天没地没边缘”,我找了好几年都碰不到一幅。充老一月底入院做清除白内障手术之前倒赐了我一小张沈从文的行草,抄黄庭坚的《清平乐》,80年代在她家里写的。充老说沈从文“写字不择笔、墨、纸,甚至写在手纸、裹物纸上”,常常只用“一枝笔,大小字全用它”。
那天大哥捧着沈先生这幅行草一遍一遍看了二十几分钟,缓缓脱下老花眼镜,两眼微微湿润了:“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窗外暮色染着霏霏细雨,咖啡桌上那两张美人老照片在灯影下泛起淡淡的灵气。“四十几年匆匆过去了。”大哥掏出一方枣红色的手帕抹眼镜,“Glasgow的冷雨下得又痴心又缠绵,像沈从文的字。”作者:董桥 来源:新民晚报
2007年06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