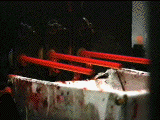.jpg)

热点排行
文人收藏 重在文化传承
经营古玩和收藏古玩的,大概没有不知道陈重远其人的。这位老先生著有《古玩史话与鉴赏》、《文物话春秋》、《古玩谈旧闻》、《古董说奇珍》、《收藏讲史话》、《鉴赏述往事》、《老古玩铺》、《老珠宝店》等收藏系列丛书。
陈先生今年78岁,身体不错,也爱说话。我们请他讲讲老北京传统收藏方面的事,他便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我国原无考古学,到了宋代才有金石学,欧阳修、李清照、赵明诚
是这方面的专家。但至今也没有收藏学,尽管收藏已日益深入民间,成为了许多人的自觉行动。说起北京收藏的历史,不能不首先提到皇家收藏。因为只有宫里,才可能汇聚天下奇珍。北京故宫是名副其实的大博物馆,奇珍异宝,无所不有。我们逛故宫看到的虽只是冰山一角,就已叹为观止。过去,这些东西秘不示人,就是封疆大吏也看不到。直到民国,故宫开放,文华殿、武英殿陈列出不少宫中藏的瓷器、铜器、字画,老百姓才开了眼界。“中国集中的文物世界少有。”陈先生感慨道:“不仅故宫里有,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颐和园、圆明园也收藏了不少,那真是浩如烟海,多如星河!”
大臣们的收藏应该说晚于皇家收藏。但大臣们学问大,他们的收藏是为了做学问,就显得格外有意义。比如乾隆、嘉庆年间有个乾嘉学派,提倡朴学,继承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治经多从文字学入手,研究金石学,使金石学再度兴起。为此,一些大臣把目光转向了青铜器。乾隆进士、体仁阁大学士阮元,就是个大收藏家。当时我国出土了一件铜盘,是西周晚期青铜器,有铭文350字,轰动一时。阮元经过研究考证,发现这是矢人将大片田地移付于散氏时所订的契约,便把这件东西定名为散氏盘。阮元还著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是研究古文字学的重要参考资料。道光、同治年间还有个陈介祺,研究秦汉书法、篆刻,他以收藏西周青铜器毛公鼎著称于世(毛公鼎是现存铭文最长的青铜器),家里盖了一座万印楼,收集秦汉印章甚多,潜心研究,著书立说。当过军机大臣的潘祖荫也是这样,收藏大禹鼎、大克鼎,研究金石,著述颇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无论收藏青铜器也好,收集古印章也好,都不是为了囤积居奇,而是为了文字学研究,为了著书立说,是和传承中国文化这个大目标连在一起的。这种收藏无疑大大提高了收藏的含金量。
收藏还有一个功能——鉴赏。比如家庭的摆设:条案、掸瓶、字画等,有的有实用价值,有的纯粹是为了鉴赏。可以说,相当多的人搞收藏,是出于赏鉴的目的。有了这个目的,收藏才能够普及,成为一般达官贵人附庸风雅的追求。因此,琉璃厂文化街才会应运而生。
北京原来商业不发达,白云观、白塔寺……是庙会,过年过节才摆摊设肆;骡马市、粮食店街、猪市大街……清早开市,日中就收摊。到清初顺治时期,汉人迁到城外,旗人住进城里(城里指前三门一带),形成了东富(买卖人)西贵(当官的)的格局。受此影响,乾隆时“东单、西四、鼓楼、前(门)”成了商业兴盛之地,而以卖书籍、古玩、字画、碑帖、文具为特色的琉璃厂也出现了。这时的琉璃厂,固然有行商作贾的市场功能,那些喜收藏字画、古玩的达官贵人时时光顾,文人墨客也常常到此,同时还兼具其他功能。举例说,当时北京没有图书馆,要看书,只有到琉璃厂买书,琉璃厂就是图书馆;当时也无博物馆,琉璃厂古玩铺就是博物馆;要看字画碑帖,也要到琉璃厂南纸店(南纸即宣纸),南纸店就是美术馆。这些独具的功能,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活动,琉璃厂因此才被叫作文化街。
眼看过年了,一说起琉璃厂,陈先生自然就想起厂甸庙会。每年正月十五之前的厂甸,既是平民百姓的乐园,也是太太小姐、达官贵人以及文化人最开心的去处,人们各取所需,小则买一串糖葫芦一个风车,中则买几本旧书几枚古钱,大则买一两样珠宝翠钻。一些大文化人常逛厂甸。官员到厂甸,关注的就不是书册,而是珠宝了。李鸿章在火神庙,给他妈买过一个翡翠镯子,这个镯子排第二,排第一的西太后戴着呢!那年月做珠宝生意的,一个春节做的买卖,够全家一年的开销了,有的甚至发了大财。
漫谈中,陈先生感慨地讲了一个故事,前面提到的潘祖荫,研究金石卓然成家,为人也克勤克俭。他无子女,过继了弟弟的一个孩子。他死后,他的后代不辱先人,竭尽全力保护大禹鼎、大克鼎。日本侵略时期,把鼎埋在地下,威逼利诱,不动声色,解放后献给了国家。现大禹鼎藏国家博物馆,大克鼎藏上海博物馆。这样的收藏家才真正是有松柏气节的人。
2006年02月05日